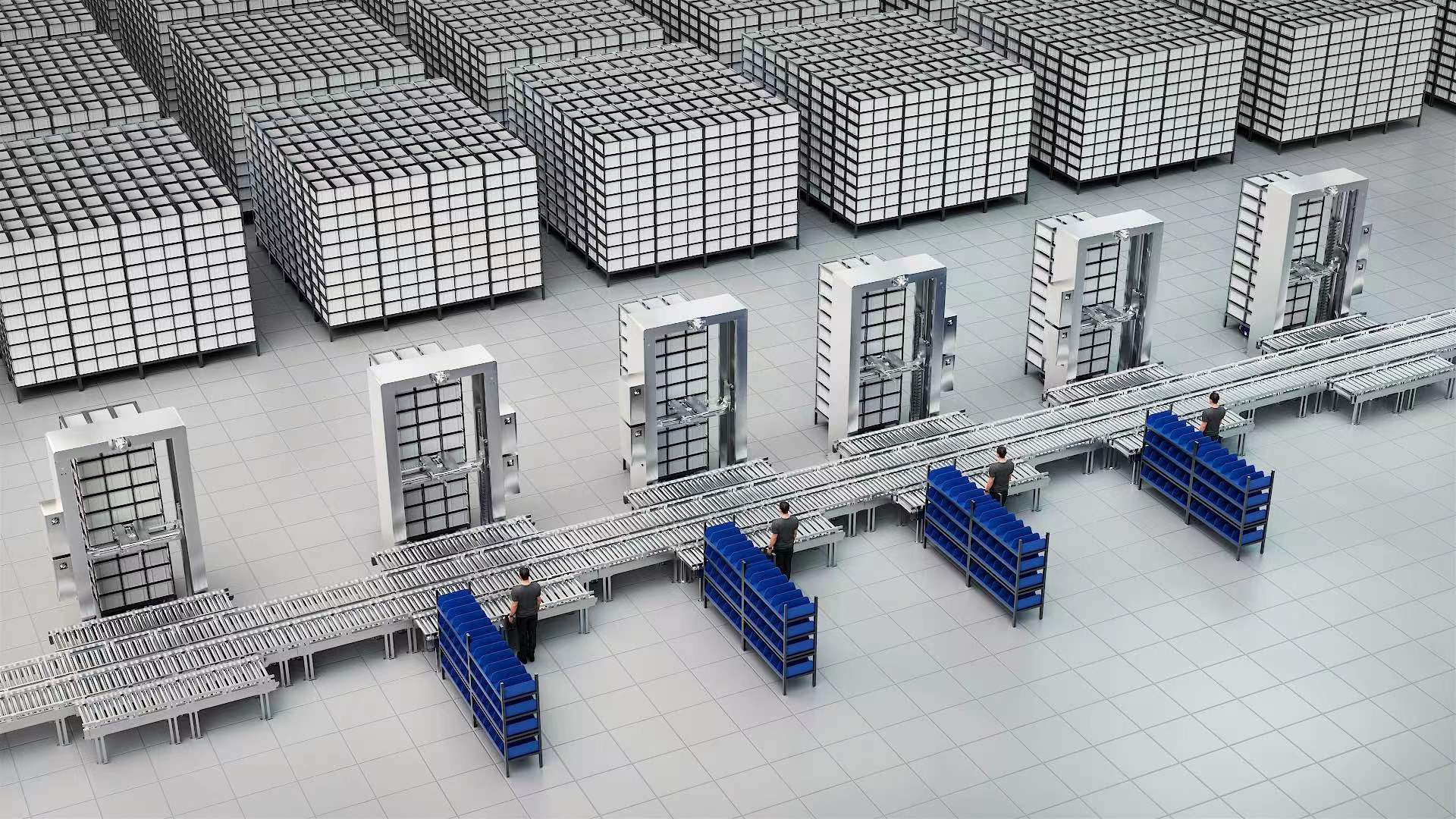相關數據顯示,機器人項目上馬的首筆支出在汽車行業中可以占到當年總支出的20%~25%,有些行業甚至可以達到70%~80%。
另外,由于需要長期維護,其間不斷發生零件和維護等人工成本。對使用廠家而言,機器人生產線發生各種成本在購買和使用產生的比例為1:10左右。
因為擁有在驅動和控制產品上的先發優勢,新時達進入機器人產業曾一度被看作是“順理成章”的新型產業拓展路徑,但公司仍是“高成本投入研發領域”。
即便如此,業內人士仍看好這一市場的高增長率,他們的普遍觀點是增長速度在30%左右。
工業機器人產業最大的效益或許來自使用者。雖然投入成本很高,但根據業內人士的估計,機器人產業一旦投入使用,對使用者而言,輻射價值可以達到投入成本的數十倍。
投資機構對機器人市場不斷增加的另一信心來自勞動力缺口的不斷擴大。“如果以每年1000萬人的勞動力缺口和一臺工業機器人抵用2~3個熟練勞動力來計算,至少每年需要400萬臺工業機器人才能足夠抵消現有的生產力。而目前機器人規模僅有5萬臺,未來市場還有百倍的增長空間。”
但在產業投資人看來,預測的數字與現實的生產能力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采取“審慎”的態度。
“國內工業機器人可投資的企業數量仍不會超過100家。”李笙凱說,雖然,國內機器人板塊上市公司的PE值都在50以上,PS值則大于10。只有工業機器人的產業以每年50%的速度發展,才能完全抹平眼下的“過熱狀況”。
由于機器人產業的高門檻、高投入、低產出的經濟特點,以及對使用客戶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對主導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決策者而言,如何引導產業介入者的“熱情”,是個不小的挑戰。
在主導上海機器人產業園的發展過程中,李臻就一直面臨園區的兩個問題:招誰進入園區?土地和廠房的空間設置在何處?前者對于園區的升級和產業引領能力至關重要,后者會牽涉園區配套和綜合設施等場域問題,諸如動遷、征地等難題。
他漸漸地發現,一些創業團隊僅僅擁有某種“概念”。
李臻回憶,項目代表通常會解釋某個概念,這樣的概念將代表未來機器人產業發展的趨勢。對方往往精心準備,“我的項目,也就是你們產業園所欠缺的項目”。
他說,自己與對方洽談時所面臨的困境,也就是園區發展的困境,究竟是選擇什么樣的產業?
數年前,李臻碰到了一個心動的“減速機項目”。在多輪談判接觸下來后,上海機器人產業園最終放棄了引進這一項目。“在多輪專家評議后,我們發現對方想要生產的設備僅僅是低端減速裝置。”李臻說。
園區招商過程中,李臻經常碰到這樣的談判對手。他們雖然自主創業,卻擁有在諸如瑞士ABB等世界機器人四大生產商之一的豐富工作經驗;他們雖然團隊規模不大,卻聲稱將帶來數億的產值能力。
“防不勝防,只有提高自身的鑒別能力和職業嗅覺。”李臻說,產業園在行業發展過程中要想成為“行家”,需要借助“外腦”,即專家和專業咨詢公司的建議可以用來評估產業的真正意義。
如果將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在全國視野下進行對比,周朔鵬認為,由于各地產業政策的不一致,扶持力度不一致,導致各區域在發展機器人產業時出現“市場失序”。
周朔鵬所說的“失序”代表便是生產沒有市場競爭能力產品的廠家,但這樣的廠家可能會“盈利”,它們的盈利能力不在于市場,而是拿政府補貼。周朔鵬認為,此舉對于產業發展未必有利,它最終要回歸到市場和技術上來。但在受訪中,也有初創型企業表示了這樣的想法,在有能力贏得市場之前,可以先小步快跑,這對小型機器人產業公司來說,利用所有的有利條件,也不失為一種發展的戰略,等到實力增強后再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